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某“名女人”的访问,据说伊向被冠以“IT界第一美女”的称号。Lorelei说:“这个职称真搞笑,IT界美女,不是跟清华的校花一个概念吗?”说完了马上掩嘴:“我这是不是太刻薄了?”其实在IT界供职的,美女大有人在,只不过都不够她爬的高。按着职位年龄性别这么一筛,剩下的只能是她了,张朝阳虽然敢于把自己扒光了上时尚杂志封面,你也不能不把人按男的算啊。她这个第一,有点象《我爱我家》里付名老人搞的家庭吉尼斯,说自己是“全家,活着的人里面,岁数最大的”。真是,关起门来,谁不是皇帝?另外,身在IT界,大家比谁长得漂亮,也实在有点无厘头。你最漂亮了,又怎样呢?色相并不能当饭吃,除非你打算出卖它。在自己圈内自娱自乐也就罢了,残疾人现在也兴有个运动会什么的。但若真要出来混,便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没理由象当年考中学一样,少数民族加几分,二级运动员又加几分,观众的反应最无情。郭晶晶锋头最劲的时候,恨不能一天踩三个场子,盛装出席各式各样的发布会,背后有形象设计师也不管用,生是把个fendi穿得象买豆制品的售货员。还不许我们笑,好像笑了就是对世界冠军不敬似的。其实泡在泳池里一天,她就仍是头顶光环的小公主,别说跳水这样的高难度动作,即便摊煎饼炸油条的小贩,在自己的岗位上,手势纯熟了,一样散发工作美。谁让你踩过这条线?而且还是为着名与利,更加不堪。
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某“名女人”的访问,据说伊向被冠以“IT界第一美女”的称号。Lorelei说:“这个职称真搞笑,IT界美女,不是跟清华的校花一个概念吗?”说完了马上掩嘴:“我这是不是太刻薄了?”其实在IT界供职的,美女大有人在,只不过都不够她爬的高。按着职位年龄性别这么一筛,剩下的只能是她了,张朝阳虽然敢于把自己扒光了上时尚杂志封面,你也不能不把人按男的算啊。她这个第一,有点象《我爱我家》里付名老人搞的家庭吉尼斯,说自己是“全家,活着的人里面,岁数最大的”。真是,关起门来,谁不是皇帝?另外,身在IT界,大家比谁长得漂亮,也实在有点无厘头。你最漂亮了,又怎样呢?色相并不能当饭吃,除非你打算出卖它。在自己圈内自娱自乐也就罢了,残疾人现在也兴有个运动会什么的。但若真要出来混,便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没理由象当年考中学一样,少数民族加几分,二级运动员又加几分,观众的反应最无情。郭晶晶锋头最劲的时候,恨不能一天踩三个场子,盛装出席各式各样的发布会,背后有形象设计师也不管用,生是把个fendi穿得象买豆制品的售货员。还不许我们笑,好像笑了就是对世界冠军不敬似的。其实泡在泳池里一天,她就仍是头顶光环的小公主,别说跳水这样的高难度动作,即便摊煎饼炸油条的小贩,在自己的岗位上,手势纯熟了,一样散发工作美。谁让你踩过这条线?而且还是为着名与利,更加不堪。
还有些名头也够难为情的,比如网络歌手——即是业余歌手了,登不得台面,那几位还真不争气,前阵子浮出水面开了一场演唱会,结果惨糟滑铁卢。又比如美女作家——多半美也美不过人家,写又写不过人家,只好算美女作家,意思就是说:在作家里,我算长的顶不错了,美女里面,就数我识字多。哪一行的状元都不好当,只好玩票捞过界。连选美也可以再设多几个奖项:除花魁外,再评选最男人的女人,和最女人的男人,大块分猪肉,皆大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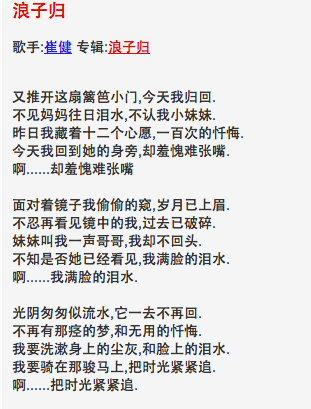 跟蟹哥借了一本小说看,时至今日,还肯买小说看的人,试问若不是有文化,那还能是什么呢?连我这个电脑盲都改成在网上看了。以前看过这个作者的一本书,还不错。这本就觉得有点矫情了,来回来去那点子事。其实除了若干大师,谁写东西不是那三板斧,虽然不一定是自传,也尽量挑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写。就看那些事你感冒不感冒——咱们外行看书,可不就是为了消遣。作者反复地回忆自己的无悔青春,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,宿舍同学的情谊,青梅竹马的恋情??恨不能回到当初的样子,我统共不能理解。我自小是个不爱念书的孩子,我的大学生活虽不至于痛苦,但也殊不愉快,巴不得快快熬过去。一向做什么都拖拉,唯独办离校手续,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积极奔走,一个上午就盖妥十几个戳,卷了铺盖逃走,同学有时开玩笑说:多少年后再回来的时候——我立刻骇笑着说:不回来了,再不回来了。
跟蟹哥借了一本小说看,时至今日,还肯买小说看的人,试问若不是有文化,那还能是什么呢?连我这个电脑盲都改成在网上看了。以前看过这个作者的一本书,还不错。这本就觉得有点矫情了,来回来去那点子事。其实除了若干大师,谁写东西不是那三板斧,虽然不一定是自传,也尽量挑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写。就看那些事你感冒不感冒——咱们外行看书,可不就是为了消遣。作者反复地回忆自己的无悔青春,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,宿舍同学的情谊,青梅竹马的恋情??恨不能回到当初的样子,我统共不能理解。我自小是个不爱念书的孩子,我的大学生活虽不至于痛苦,但也殊不愉快,巴不得快快熬过去。一向做什么都拖拉,唯独办离校手续,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积极奔走,一个上午就盖妥十几个戳,卷了铺盖逃走,同学有时开玩笑说:多少年后再回来的时候——我立刻骇笑着说:不回来了,再不回来了。 娱乐新闻里播出郑智化复出歌坛的消息,一边把他昔日的风光数说一遍:当年凭《水手》名噪歌坛,足足红了十年——我倒真吃了一惊,什么?一个《水手》,一个《星星点灯》,就能叱咤十余年?那时的歌坛可真好混。一直都很嫌这个人,据说他连五线谱也不识得,所谓作曲是自己哼出调子,由别人执笔纪录。词曲均很粗糙简陋,无非是打着快板洒狗血,我听着简直要发出冷笑来。不过因为他是一名伤残人士,一直不太好意思刻薄他。偏偏那时有点歪风邪气,但凡有人对社会表示不满,立刻就被封为忧国忧民的大师,传说他当年离开歌坛,是因为不堪成名的压力——也无非就是有人当街叫出他名字,连绯闻也未见传过,什么压力? 可见不是一个明白人。
娱乐新闻里播出郑智化复出歌坛的消息,一边把他昔日的风光数说一遍:当年凭《水手》名噪歌坛,足足红了十年——我倒真吃了一惊,什么?一个《水手》,一个《星星点灯》,就能叱咤十余年?那时的歌坛可真好混。一直都很嫌这个人,据说他连五线谱也不识得,所谓作曲是自己哼出调子,由别人执笔纪录。词曲均很粗糙简陋,无非是打着快板洒狗血,我听着简直要发出冷笑来。不过因为他是一名伤残人士,一直不太好意思刻薄他。偏偏那时有点歪风邪气,但凡有人对社会表示不满,立刻就被封为忧国忧民的大师,传说他当年离开歌坛,是因为不堪成名的压力——也无非就是有人当街叫出他名字,连绯闻也未见传过,什么压力? 可见不是一个明白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