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时候我真不爱买煎饼。爱吃管爱吃,但是那些琐碎的要求真令人头痛。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疙瘩的人:加两只蛋,不要葱花,要香菜。少放一点黄酱,多放一点辣酱……把个小贩BRIEF的头晕眼花。煎饼摊得太过熟手,一不留神就搞错,只得浪费了重来。因此每个环节都要牢牢盯住,我比小贩更紧张。买衣服也是,嫌这件衣服有花边,那件多一条腰带,可不可以不捏那么多褶?每年买那一双凉鞋,最头疼:黑色,软的半跟,缚带,足面两根细带子,不要漆皮,不要蝴蝶结,不要金属扣,不要……本来穿得下的就不多,真是的。
如果由此推论,我一定是个不好相与的人。连对一只煎饼都百般挑剔,还肯放过谁?但是我并不太挑剔人——惹不起我还躲得起,说不通就不要费那么多口舌,别劝,千万别劝。正像我苦口婆心告诉客户:不要妄图去做消费者教育,您不趁那个钱。
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,志趣相投,习性一致,混久了连口头语都一样,加上无数的典故,好似黑社会的切口,外人根本插不进来。有时看BLOG,发现基本上就是两伙子人:意气风发的IT青年,和小布尔乔亚的记者编辑,谁的眼角里也不夹人。查理每看了人家的BLOG,回来就嫌弃我庸俗,我唯唯诺诺,也并没从此思上进。在我们这个圈子里,被人说庸俗恐怕不是一件坏事呢。
已经荣升师奶,谁还争这种意气,唯独有一次动了真气:长假的某一天,从妙峰山回来,想找个地方打牌,误打误撞去了“雕刻时光”,一坐下就开始洗牌,活象四个急色鬼,一边把服务员叫过来要点心。服务员长辫子碎花袄,打扮得跟清倌人相仿,脸上似笑非笑,眼角高高地说:“对不起,我们这里规定不能打牌,那边有其他游艺活动您可以选择。”“其他”二字说得很重,分明是嫌俺们低俗呢。我们即刻收拾东西退席。什么玩意儿,这种腻腻歪歪的文艺腔调,使给那起没见过世面的学生看去,我很看不惯这个浪样子。丫们倒不低俗呢,一帮学生打扮得跟五四青年款式和不三不四的穷老外搂一团,当咱们北京城是长三堂子呢。我一路迁怒开车的猪老:“就不应往海淀区来!”
真的,一进这个区,说不出的不自在,不过有几十所大专院校,也不管良莠,马上标榜人文气息,我至受不了那种故作清高的学生气。谁没当过学生?不是我说,我们彼时虽然也幼稚,至少不那么张狂。也许我们没能在海淀文化圈里浸淫,所以拿不出那个劲儿来,也是有的。
所以我顶不同意世界大同这件事,大家最好都待在自己的圈子里,免得互相看白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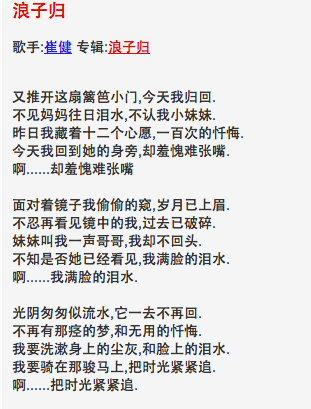 跟蟹哥借了一本小说看,时至今日,还肯买小说看的人,试问若不是有文化,那还能是什么呢?连我这个电脑盲都改成在网上看了。以前看过这个作者的一本书,还不错。这本就觉得有点矫情了,来回来去那点子事。其实除了若干大师,谁写东西不是那三板斧,虽然不一定是自传,也尽量挑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写。就看那些事你感冒不感冒——咱们外行看书,可不就是为了消遣。作者反复地回忆自己的无悔青春,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,宿舍同学的情谊,青梅竹马的恋情??恨不能回到当初的样子,我统共不能理解。我自小是个不爱念书的孩子,我的大学生活虽不至于痛苦,但也殊不愉快,巴不得快快熬过去。一向做什么都拖拉,唯独办离校手续,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积极奔走,一个上午就盖妥十几个戳,卷了铺盖逃走,同学有时开玩笑说:多少年后再回来的时候——我立刻骇笑着说:不回来了,再不回来了。
跟蟹哥借了一本小说看,时至今日,还肯买小说看的人,试问若不是有文化,那还能是什么呢?连我这个电脑盲都改成在网上看了。以前看过这个作者的一本书,还不错。这本就觉得有点矫情了,来回来去那点子事。其实除了若干大师,谁写东西不是那三板斧,虽然不一定是自传,也尽量挑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写。就看那些事你感冒不感冒——咱们外行看书,可不就是为了消遣。作者反复地回忆自己的无悔青春,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,宿舍同学的情谊,青梅竹马的恋情??恨不能回到当初的样子,我统共不能理解。我自小是个不爱念书的孩子,我的大学生活虽不至于痛苦,但也殊不愉快,巴不得快快熬过去。一向做什么都拖拉,唯独办离校手续,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积极奔走,一个上午就盖妥十几个戳,卷了铺盖逃走,同学有时开玩笑说:多少年后再回来的时候——我立刻骇笑着说:不回来了,再不回来了。